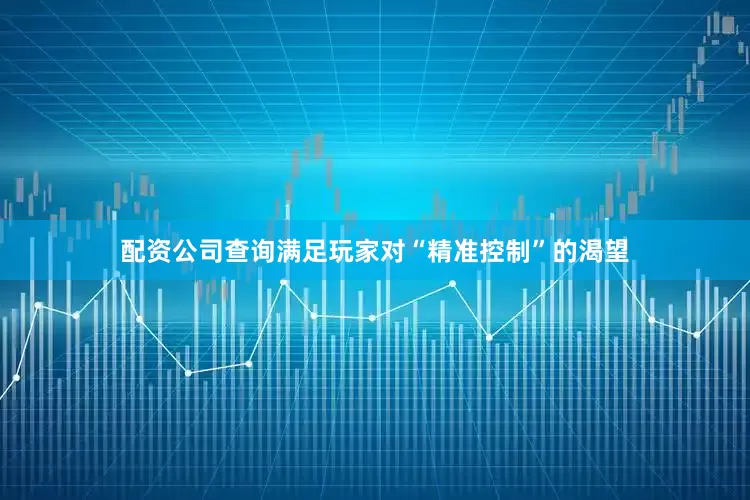孙维世(1921-1968)
■ “我们两家是世交啊”
1950年的炎炎夏日,我年仅8岁,便跟随双亲乘坐水路船只,自重庆一路驶向武汉,继而又转乘火车抵达了北京。自此,北京便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,我在此地定居下来。
我抵达北京后观看到的首部剧目,便是这部民族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。那天,当我抵达首都剧场的门前,门卫拒绝了我入场的请求,理由是儿童不得入场。那时的我正值生长发育的初期,体型瘦小,头部略显细小。父亲见状,急中生智,便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受赠的观众,得到了孙维世导演的赐予。他取出装有赠票的信封,展示给门卫,信封上印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官方标志,信皮上清晰标注着我父亲的名字,右下角还签名了“维世”二字。
此法果然有效,他们便准许我随父母一同进入。我那颗幼小的心,原本紧绷,此刻却渐渐放松,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那部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系由李季的长诗改编而成,导演并非孙维世,亦非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剧目,而是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义上演。或许因孙维世与编剧于村关系密切,故而分配到了较多的门票,便慷慨地分赠给亲友,我家也因此有幸获得。
自那之后,我意识到我们家有望获得免费门票,得以观赏演出。所谓的赠票,我父母称之为“兰姑姑”。虽然我始终未曾见过兰姑姑,但她的亲妹妹,我父母称作“粤姑姑”的,却多次莅临我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自然明白了兰姑姑的真名叫孙维世,而粤姑姑则是孙新世。

左起:孙维世、邓颖超、周恩来、孙新世
晚出生的我,对上一代的故事,仅限于听闻。我的祖父刘云门,早在1932年便离我们而去了。而我自己,在祖父逝世十年后才呱呱坠地。近几年,粤姑姑自美国归国,约我在贵宾楼的红墙咖啡厅会面,一见我,她便热情地高声说道:“心武,你知道吗?我们两家可是有着悠久世交呢!”
总体而言,兰姑姑与粤姑姑,她们还有三位兄弟,他们的父亲孙炳文与母亲任锐于1913年在北京结为连理,我祖父刘云门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。婚宴之后,一张在什刹海北岸会贤堂饭庄前的合影至今仍保存着。1922年,孙炳文与朱德前往德国前夕,曾短暂寄居于我祖父家中。1924年,我祖父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。翌年,母亲遭遇困境,被孙炳文与任锐接至其家中居住。然而,不久后他们便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,母亲随即被安排至任锐的妹妹任载坤——冯友兰夫人——处暂居。因此,在我步入文学圈后,便将宗璞尊称为“大姐”,然而却遭到母亲的责备,她认为我应该称之为“璞姑姑”。兰姑姑、粤姑姑均系宗璞的表姐,她们与宗璞同辈。

孙炳文与任锐的结婚照片中,最右一排的第二个位置尊荣地坐着证婚人刘云门先生。
■ “我要兰姑姑的票”
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以来,孙维世导演执导的首部作品便是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该剧的门票也辗转送至我家,然而,哥哥姐姐却先行观看了,我未能如愿。那时,我父亲先是服务于海关总署,后转至外贸部任职。兰姑姑赠送的票券,似乎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父亲的工作单位。记得有一次,我看到父亲下班时从衣兜中掏出一个信封,便兴奋地跳脚高呼:“我要兰姑姑的票!”然而,父亲却向我摇了摇头,向母亲解释道:“这次并非是票,而是一封信,邀请我前往她家共进便餐。”
兰姑姑与粤姑姑均以“天演兄”称呼我父亲,而对我母亲则尊称为“刘三姐”,或者简单地以“三姐”相称,这是因为在我母亲娘家,她是排行第三的女儿。后来我才了解到,兰姑姑与著名演员、饰演保尔的金山先生喜结连理,他们的婚礼早已举行,而特别邀请我父亲出席,恐怕是对这份世交的深厚情谊表示的重视。那日,父亲带回了一瓶葡萄酒,自豪地提及兰妹(他总是这样称呼孙维世)曾告诉他,这瓶酒是周总理所赠。不久将有贵宾到访,父亲便高兴地开启这瓶美酒,与宾客们共享这份喜悦。

1950年《保尔·柯察金》影照
主演:金山、张瑞芳

孙维世和金山
父亲归家,手中捧着兰姑姑所赠的戏票,笑着对我说:“这全是你的!”原来,兰姑姑将她在舞台上演绎的儿童剧《小白兔》制作成了舞台艺术片,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精心拍摄。我遂邀约了两位同学,一同前往新街口电影院。那日,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预映活动,正式公映前的招待场。我听见父亲与母亲低语:“兰妹自15岁起便在上海登台演电影,她对电影艺术可谓是了如指掌,拍摄起来游刃有余。”遗憾的是,此后兰姑姑并未再涉足导演电影领域。
兰姑姑再一次赠票,是她导演的果戈里的名剧《钦差大臣》,我高兴地跟母亲去东单拐角那里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用剧场观看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,全剧演到最后,台上台下都在笑,忽然一个大声说:“为何而笑?笑自己吧!”随后,所有演员以各异姿态定格不动,观众们也瞬间陷入沉默。随着帷幕缓缓落下,观众们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兰姑姑,于1939年远赴苏联深造戏剧,恰逢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38年仙逝。当时,其嫡传弟子列斯里正值风华正茂之际,兰姑姑得以成为他的学生,从而有幸继承并深入学习斯氏体验派戏剧的真谛。
■ 周总理劝:好好说话
1956年夏日,兰姑姑自青艺别离,转至新成立的中央实验话剧院。该剧院由资深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院长,兰姑姑则担纲总导演之职。
在新剧院,她仍不时给我父亲寄戏票。她根据剧作家岳野的剧本,导演了《同甘共苦》。但是父亲不让我去看。这个戏写的是一个建国后已经升到相当高职务的干部,他参加革命前,父母包办婚姻,娶了一个乡下没文化的姑娘,他后来就离了婚,与革命队伍中有知识的红颜知己缔结良缘。这样的人物经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,但是剧作家却结撰出以下情节:这位干部下乡进行工作指导时,意外地遇到了前妻。为了使剧情更加尖锐和复杂,剧本中还描绘了干部的母亲,这位母亲一直由前妻悉心照料。为了不让婆婆的心情受到影响,前妻隐瞒了他们离婚的事实。以至于当干部回到家乡指导工作时,他的母亲还误以为他是回来与媳妇团圆的……

《同甘共苦》剧照
张颖女士,曾服务于周总理并在其中南海西花厅居住地出入自由,在观看《同甘共苦》一剧后,于周总理面前与兰姑姑发生了争执。两人年纪相仿,张颖女士年轻时亦曾登台表演,她认为此剧不宜搬上舞台,内容被认为不健康。兰姑姑反驳道,展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命运的曲折何来不健康之嫌?并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。周总理见状,劝告双方保持冷静,理性沟通。
■ 最后获兰姑姑戏票
那一次,我最后一次手握兰姑姑赠送的戏票,已然是1962年的时光。那日,我得以观赏她执导的《黑奴恨》,这部作品是根据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精心改编而来。追溯至1907年6月,欧阳予倩、曾孝谷、李叔同等先贤所创立的春柳社,在日本首次将这部改编的五幕新剧搬上舞台。岁月流转至1961年,欧阳予倩再度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与润色。
1961年,欧阳予倩尚健在,彼时他担任实验话剧院院长,已是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。而兰姑姑比他晚出生了三十余年,当时年仅40岁。执导这样一位中国话剧界的前辈巨匠的剧作,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。2018年,我在电视上观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资深演员田成仁的一段访谈,他讲述了57年前在《黑奴恨》中的演出经历。原来,在排练这部剧时,原本选定的主角是一位体型胖壮、颇富经验的演员,他的体型与原著小说中的描述相符。然而,导演却总觉得这位演员并不合适,于是决定让他停下。当时,兰姑姑正在剧院里排戏,剧院的每个人都想一睹她的风采,田成仁也不例外,他躲在一旁默默观看。没想到,兰姑姑一眼就发现了田成仁,并点名让他进入排演空间,为大家展示一段表演。田成仁回忆说,那天他感到非常害羞,试图逃避,但《黑奴恨》的排练也因此暂时搁置。

1961年首演话剧《黑奴恨》
约莫半月之后,剧院再度启幕排练,并公布了角色分配,男一号黑奴汤姆将由田成仁出演!由此可见,在停排期间,兰姑姑不断探索舞台艺术的创新。尽管田成仁的身材瘦高与原著中的汤姆形象有所出入,但她此次并不追求外在的相似度,甚至也不拘泥于单纯通过体验来挖掘角色的“种子”与“动机”。相反,她广泛借鉴了布氏体系的表现派手法,在人物的站姿、动作,以及与其他角色的形体交织、搭配、互动中,力求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雕塑感。
1964年,兰姑姑毅然踏足彼时的石油重镇大庆,与那里的工人们及他们的家人共同生活、共同劳作。次年,她挥毫泼墨,创作了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,并由金山担纲执导。1966年的上半年,这部作品携带着她的心血进京献演,一时之间引起了轰动,好评如潮。这无疑是她努力为中国话剧领域开辟新篇章的杰出力作。

周总理亲临大庆进行视察,期间亲切接见了正深入大庆地区生活的孙维世同志。
然而,自1963年起,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,此后也就再也没有收到兰姑姑赠送的戏票。
我偏爱那些怀抱坚定信念的人,那些对自身事业深信不疑的人。当一个人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,他便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658配资-配资炒股知识-正规的配资公司-专业网上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